猎手
…
“听说昨夜狼来了,咬伤了一头猪?”
“咬伤了一头母猪。那不是?就在那猪场里咬的。”他用手往水库右面指了指。我一看,那里果然有一排猪圈,整整齐齐,阳光下白粉墙明晃晃的。
“快!猪场狗叫了,一定是狼来了。”
大钟告诉我,朱扒福是漏网地主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流窜到安徽合肥,搞了许多破坏活动,民兵追了千多里路才把他抓回。一年前,他喂的这头母猪生了小猪,妄图抬高市价,投机倒把,群众气不过,就把它没收了。现在这头母猪又要生小猪了,他想趁昨晚狼没咬死,再来补一把火。
那是种么样的风啊?”
“上来,咱们一块于吧!”
我一听,冲上一股劲:“我也去。”
“唔,”他好象没听见似的说,“大队生猪刚上《纲要》,昨夜那头母猪,再不要好些时,就要生小猪,要是叫狼叼走了,该有多大的损失不出来转转,睡不着”
“山区建设,不搬石头搬啥?”我气愤地说。
风吹月转,明月挂在天盖的中央。山区的夜静极了。我们转身来到猪场的大沟边。沟里一垄垄新开的梯田,好象一直要延伸到青灰色的天空。田头一块大石岸上,刻着三个大字“民兵田”。
“是我一时的糊涂呀!”
看他这么痛快,我也上来了痛快劲,就这么一会,我们好象相识了很久似的,无拘无束地聊了起来。
“你不警惕,它就出来捣乱。”他若有所思地说,“今晚我还要去守猪场。昨天搞破坏没搞成,今晚可能还要来,看我一枪嘣了它!”
“莫……莫开枪呀!我是朱扒福哇!”
才到岩河岭,我就听人向我介绍:还在大钟十几岁的时候,他爹就在鹞落坪、桃花冲一带跟随红军打游击。有时夜里带回几个拿枪的人,天不亮又走了。大钟问:“爹,你在外面做的什么生活啦?“打狼!”爹告诉他:狼可多着呢,这辈子打不了,长大了要接过爹的枪打下去……
“它想把那猪赶回去,没来得及咬死。”
“披着人皮的狼唦!毛主席号召我们农业要大上快上,现在春耕农忙的时候,这种狼最喜欢出来。走,往水库上转转。”
“谁?”大钟一声吼,猪栏里那个灰影缩了下去,只听见“当”的一声,好象有根棍子掉到地上。
月光把岩河岭刷得明明净净。初春天气,高山上寒气逼人,一阵风过,满山满岭松涛哗哗作响。我裹紧大衣,跟在大钟后面,在猪场巡回。搬了一天石头,这会儿只感到两腿软,身上酸,眼皮打架,想睡觉。大钟却把一身裹扎得利利索索,挎着一支“半自动”,挺着胸脯,四处张望,那劲头,就象刚吃饱了、睡足了一样。
不做声,要开枪了!”大钟把枪栓拉得直响。
“你!?他把一块石头“咚”地放下,笑眯眯地说:“好哇,欢迎指导!”
猎手大钟,是岩河岭上有名的神枪手。据说他百步灭灯手举鹰落。我想:这不成了杨子荣吗?巴不得早点就认识他。
“是队里派你来守夜?”
“那你明天该休息一天啦!”
大钟把手一摆,端着枪大步流星地奔到了猪栏门口。
“你怎么跑到我们没收你的这头母猪身边来了?快讲!”
“去年冬天开的?”
刚登上猪圈背后山坡,一股冷风钻进脖子,我不由得打了个寒噤,跟上一步:“狼在夜里是什么样子?”
“幸好没咬死。”
那是岩河岭上入春以来第一个晴天。
啊!我明白了:为什么大钟对狼那么痛恨?对狼的习性又那么熟悉?明白了他为什么练出这么一手好枪法?为什么白天干活不知累而夜里又这么精神抖擞地守卫着岩河岭……一股暖流流遍全身,驱走了寒意,赶跑了瞌睡。月光下,我看见那巍峨屹立的水库大坝,那层层铺垒的大寨梯田,那盘山环绕的渠道,那满沟满畈青幽幽、黑压压一大片的庄稼,骤然觉得:种原来离不开打狼!这会儿,那些两只脚的狼,正在黑暗处咬牙切齿,梦想着钻出来搞破坏呢!
“阶级敌人本性不变嘛!”大钟对我大声说。
赶到猪场,朦胧中只见一个五尺高的灰影,一边招架狗子,一边跃进了猪栏,随着就是一阵猪惊慌的嗥叫声。
这时,火红的太阳正冉冉升起,水坝、梯田、水渠、松树……全涂上了一层金辉,满田的社员在欢笑。到处是春耕大忙的景象。
“一九七O年冬天开的,是顶着一种人造北风开的。”他诙谐地说。
“你想昨天狼没把这头母猪咬死,今晚再来补一把火,破坏生猪发展是不是?”大钟一把揪了朱扒福,“哐啷”一声关进了一间小土屋里。
大钟越讲越起劲。突然,“汪,汪,汪”一阵狗叫,大钟拉着我的胳膊说:
“这是民兵开的?”
听说省里的同志来了,我本来想去看看的,没有时间。他码好一块石头,弯下腰伸过一只手说:“来,咱们一块儿干!”
三星偏西,我俩进了屋。大钟说:“歇个火!”放下枪,往床上一倒。我也倒在床上,一闭眼,我就看见大钟在月光下巡逻的姿影,可是再细看,又好象不是大钟。一忽儿,我看他戴着八角帽,带着几个有红袖标的人走过;一忽儿,我又看他穿着解放军的军装,脚下也好象不是岩河岭,有工厂,有桥梁,有楼房一忽儿,又是原来的大钟,只见他猛地猫下腰,慢慢摘下枪,对准了水坝边上一个黑糊糊的东西……
“它用嘴巴咬住猪的耳朵,用尾巴打猪屁股,就能把猪赶走。”
“真是狡猾的豺狼!”
当时他正在水库大坝上砌石墩:光膀子,穿着一件黑夹袄,腰里紧扎一条宽皮带;一条单裤挽过膝,露出饱绽绽的两腿肉疙瘩。两个人抬着递给他的石头,他一抱就轻轻地放在石墩上了。早春天气,水库旁山头上松针还结着凌珠儿,他身上却直冒热气,看上去全不象上了岁数的人。他弓着腰从一个姑娘手里接过装满沙浆的灰桶,笑着说:“莫把肩膀提歪了,看我一个小指头把它拎上来。”话音刚落,沙浆已光光滑滑地铺在墩面上了。他正打算往回扔灰桶,“糟!—”我想这一家伙不摔了个粉碎了吗?出乎意料,他却把桶子慢慢地递到那位女社员手里,又笑着说:
望着他那高大的身影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,我暗暗想道:杉树底下长杉秧,真不愧为烈士的后代啊!
“有两只脚的狼?”
“嗯……我……”朱扒福结结巴巴。
大钟一听,原来是朱扒福,一股怒火直冲脑门顶,一步跨了过去,把瘫做一团的朱扒福提了起来,“谁叫你半夜三更来打猪的?”大钟严肃地问。
快瞄准呀”我急了。
远远地,我就看见了大钟。他还象昨天那样,敞怀穿着黑夹袄,裤脚卷过膝,站在石墩上。见我来了,笑着对我说:
“真阴险!”
“就是一小撮阶级敌人诬蔑我们英山人民学大寨只不过搬了几块石头。”
我急忙跑出去,果然见几个社员围着一只死狼,一面喷舌赞叹着:“又是打碎了天灵盖!”再一看,却不见大钟。我问社员,他们往猪场一指说:“在那边呢!”
“他们可不是这么想的。他们搞阴谋诡计啊!那时候,压力可大啦。可是我们县委洪书记领导我们贫下中农顶住了。那套复辟资本主义的货色,不顶还行?不过,我们山里人,只会搬几块石头罗”他一边说,边用手比划着。
“狼还会赶猪?”我惊奇地问。
“还是少提点,多跑两趟,莫把腰压了。”他抬头看见了我,就笑眯眯地打招呼:“张同志,你来了!”
“我来了好一会呢。”我想:他怎么已经认识我啦?真快!
我正往猪场走去,队长和大钟押着朱扒福过来了。大钟把朱扒福推到死狼跟前,队长脸上带着微笑,看了看地上的死狼,又望了望浑身发战的朱扒福,对围着的群众意味深长地说:“阶级敌人象狼一样,一有空子就钻出来破坏。我们要象大钟那样,时刻不忘阶级斗争啊……”
哥既当兵又当民嘛!——我这个老兵混在年轻伢们里头教教枪法……这田是顶着北风开的呢。”
“嗨嗨,那不碍事。”他含糊其词。
“叭——”一声枪响,我惊醒了。窗格子曚曚亮了。自己的衣服不知什么时候脱下来的,身上盖着被子。再看大钟,早走了。我正穿衣起床,听到窗外有小孩:看哟看哟大钟伯又打了一只狼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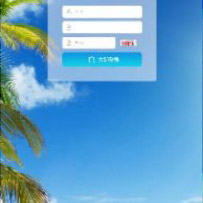
发表评论